劳动异化与劳动同意:互联网数字劳动的价值二重性辨析
来源:
发布时间:2021-04-29
点击量:4877次
- 收藏
-
微信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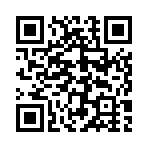
【摘要】信息社会劳动生产的扩大化,使得数字劳动广泛存在于数字资本公司、互联网平台零工、非雇佣形式的产销者等领域,并且在技术、资本和消费文化的感召下呈现出劳动方式娱乐化、劳动时空泛在化、劳动剥削隐秘化等非典型“劳动异化”的特征,成为劳动同意缔结的前提。在平台“去异化”策略和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感召下,劳动异化与劳动同意并存于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劳动关系中,呈现出基于不同主体需求的数字劳动价值二重性特征,并引发关于社会文化责任旁落的反思。
自达拉斯·斯麦兹的盲点之争后,受众研究实现了从“效果”到“劳动”的转型,劳动商品化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。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,这种劳动的商品化表现为在各社会生产领域里的“数字劳动”,凸显了互联网平台作为“新的社会生产场域”的典型特征。“20世纪70年代以降,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,在社会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。信息的生产、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”[1]。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互联网公司,都被嵌入到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生产链条之中,专业化生产向“同侪生产”的演化,催生了新的劳动主体与劳动关系,带来了二者之间价值分立的再思考。
一、享乐还是剥削: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
(一)数字劳动的界定
数字劳动是信息化社会中对劳动形式的新界定,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安·福克斯(Christian〓Fuchs,2014)认为,“ICT行业全球价值链从低端到高端整个链条上所牵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,均属于‘数字劳动’”[2]。马里索尔·桑多瓦尔(Marisol
Sandoval)将数字劳工定义为:“将ICT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,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。在她看来,资本对ICTs和数字技术的吸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空间从‘工厂车间’到‘社会工厂’的转变过程。”[3]
上一篇: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多元主体责任规
下一篇:风险社会视域下深度报道再审视
会员登陆
热门排行












 添加表情
添加表情




查看更多评论